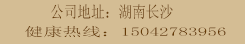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利息与价格 > 利息与价格历史 > 德商周浩中国央行加息几无可能公开市场利
当前位置: 利息与价格 > 利息与价格历史 > 德商周浩中国央行加息几无可能公开市场利

![]() 当前位置: 利息与价格 > 利息与价格历史 > 德商周浩中国央行加息几无可能公开市场利
当前位置: 利息与价格 > 利息与价格历史 > 德商周浩中国央行加息几无可能公开市场利
近期,中国基准利率是否存在调整空间再度引发市场热议。德商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认为,中国加息机率很低,“几乎没有可能”。
在周二举行的德国商业银行中国年经济展望会议上,周浩还介绍了该行对明年中国经济和市场展望情况。
周浩认为,今年政府将实施更严厉的金融监管,推进“去泡沫”。但在监管和市场不断博弈下,债市“熬杠杆”过程将持续很长时间,直至新的市场变量出现。
此外,对于今年的人民币汇率、GDP增速等,周浩也给出了自己的预测。
人民币看至6.8央行“几乎没有可能”加息
周浩称,过去一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确实跟随一篮子货币指数波动,且明显看出人民币波动率开始上升。至于经济增速,6.4%的预测值反映了周浩对经济的最终看法,即去杠杆必然会带来利率的上升,利率上升的过程必然带来经济活动的下降。
利率方面,周浩预期公开市场操纵利率会呈现上行的趋势,反映出整体政策趋紧的基调,但是中国加息的机率很低,“几乎没有可能”。原因是央行有意降低一年期存贷款利率的重要性。此外对于央行而言,OMO是更加便利的操作方式。但同时,周浩认为,OMO利率今年不太可能上升到3%以上,甚至“弄不好最近的一次5个点的上调就是终点”。总体而言,“公开市场利率仍在趋紧,但目前对于利率预期有过高的嫌疑”。
债市继续“熬杠杆”
进入年以来,债市去杠杆持续推进,市场情绪也越发趋向于谨慎。周浩基于债券回购交易量数据判断,目前在监管和市场不断博弈下,债市正处于“熬杠杆”的过程中:
在过去一年多中,债券回购交易量并未出现明显的上升或下滑,从数据来看没有明显去杠杆的迹象,但是的确也没有加杠杆的迹象。现在就是熬,监管机构不断地加码或放松来煎熬大家的杠杆,投资机构也是在坚持着自己的杠杆。我个人的感觉是,杠杆率真实下滑的情况是很难出现的,可能会维持较高杠杆的状态一段时间,等待新的市场变量出现。要么是经济出现超预期的下滑(目前看来很难出现),要么是一家金融机构出了很大的问题,让市场开始担心中国市场或者是中国金融机构稳定性的问题,否则政策拐点很难出现。我们只是在互相博弈,这种博弈的过程会延续很长的时间。
近几年,中国家庭债务上升迅速,并且主要来自于房地产市场。对于很多人认为较为严峻的中国家庭债务风险,周浩有不同的看法:
这一观点拿到发达经济体,比如欧洲、美国去,很多人会提出质疑,因为家庭债务不上升意味着家庭没有消费,家庭没有消费,意味着政府要帮助它消费。因为如果家庭不背债务就是家庭储蓄率提高,那就意味着政府要帮助他消费,这就形成了政府债务。这是一个反论,即如果我们的家庭债务不上升,政府的债务就会进一步上升,因为政府要通过债务支出的形式支撑经济。这样的支撑经济的形式就是政府搞基建,家庭买房子;家庭不买房子,政府就搞更多的基建迫使你买房子。
今年是强监管的一年
周浩认为,强监管的政策肯定会继续下去,中国整个金融业未来一年还是通过股票和债券的方式来增加资本的充足率。
周浩称,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可能意味着政治层面的重新梳理,未来5年监管环境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此外,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落实监管政策,以及在落实过程中许多变量的出现可能会影响政策的推进:
落实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变量出现,尤其是一旦经济放缓就会有人跳出来说,这个政策可以再缓一缓。这是我们面临的真实监管环境。这样的环境不是与监管架构有关,而是与监管逻辑有关。整个监管的逻辑还是在梳理当中,走向更加成熟的监管还需要时间。
周浩认为,总体而言,中国的复兴和中国整体经济进程依然表现非常完善,但短期之内如果经济触到6.5%以下或者是更低,政策可能会出现转向。
经济缺乏可预测性指标
周浩认为,年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经济预测指标的失灵,以往很多传统数据对经济的预测性已经降低,甚至“没有一个指标让人觉得经济是可以预测的”。
例如,过去预测经济常用的M2与信贷数据就出现了不协调,去年M2明显降低,如果看M2预测经济的话,经济早在去年就已经垮了,但是看信贷的话经济又很好。
此外传统的预测指标——房地产市场也出现问题:
房地产市场似乎在走软,尤其是一线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和成交量都在往下走。但是市场却没有明显的房地产市场放缓势头,因为库存很低。以往房地产市场的走软往往伴随着库存的走高,这在过去几个周期非常明显。在销量库存双双下降的情况下,怎样研究、判断未来一段房地产的走势和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问题。
此外,GDP与房地产增速的关系也变得不明确,出现了“缓慢脱钩”的现象。周浩认为,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比以前小得多。不排除房地产市场的放缓对经济可能产生向下拉动的作用,但这个拉动作用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什么是中国的未来?是雄安还是大湾?
在周浩看来,雄安和大湾区恰好代表了中国发展的两个典型模式。大湾区想推动的是中国经济以IT为基础的对外开放,强调的是创新,是市场,雄安则强调的是规划,是公共。而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当中,永远没有脱离开这两个大趋势的竞争的问题:
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内部竞争也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对外竞争,同时我们也有强烈的自我竞争的模式。
这是我们理解中国非常重要的角度。我们理解中国有时候会很自上而下,即政治怎样进行,下面怎样运行,或者是考虑很多经济政策怎样制订,但是其实现实中也会有很多地方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实际经营的模式。
中国经济和市场展望总结
德商银行认为:
去杠杆化可能会在短期内削弱经济增长。预测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4%,而年预计增长6.7-6.8%。
政府将实施更严厉的金融监管,推进“去泡沫”。因此,中国银行未来需要通过股票和债券发行来增强其资本实力。此外,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呈上行趋势,与政策整体收紧的基调保持一致。
预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走向可参考一篮子货币。年底,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将徘徊于6.80附近,双向浮动的特征更加显著。
利率上调表明美元兑人民币远期点数呈上行趋势,意味着进口商对冲成本将更高。对有美元应付款的公司而言,在美元兑人民币远期点数下跌时进行对冲将更加合理。
以下是对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的采访内容:
记者:去年信贷充量下降蛮厉害,今年您预计这种现象会持续吗?会对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吗?
周浩:信贷充量总的来说过去几年有下滑,但是过去两年还是有一点点见底的迹象,有微微的抬升,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经济在好转。但是从长期来看,它比长期平均值还是是低了不少,这是短期缓解、长期依然下滑的过程。个人判断,我觉得今年增长的信贷可能会超过14万亿、15万亿,社融也是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总的来说,目前这样一个信贷充量的节奏不足以让经济出现有意义的反转。现在出现了相对较低的改善,21、23,现在回到25,但是这一水平与此前相比的话是比较低的,以前的基本上投入一万亿的信贷可以创造七、八千亿的GDP,现在一万亿信贷出来只能创造更低水平的,两、三千亿水平的GDP,来年我觉得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善,还是会比较低。也是说明中国的债务还是相对比较高。对债务有另外一个反论,中国的储蓄率还是很高,站在这个储蓄率的基础上,中国的债务还是可以维持,不会崩,但是会慢慢地在债务问题上出现日本化进程,但时间会比较长。我个人的判断是未来一年信贷水平会比较高,GDP还是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态势,反映整个经济结构相对缓慢的转型或者是目前的状况,即只有超额的信贷才能创造出超额的经济增长。
记者:您好,想请问一下今年会有哪些投资的机会?
周浩:我认为投资永远不要跟着大多数人,如果跟着的多数人往往输得很惨。另外投资要会止损,不会止损的投资不是好投资。未来一年我个人认为股市会有表现,短期内股市会有表现。第二我们需要看到一季度底的市场状况,如果说市场现在的判断在第一季度能被印证,那市场可能会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谨慎一点。如果市场一季度表现平稳,可能股市的机会会大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我个人还是认为今年最大的机会来自于市场的一个“惊喜”,目前的惊喜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downsidesurprise。因为目前upsidesurprise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我认为市场的惊喜只有向下的惊喜,就是经济会出现一个突然的下滑,引发探讨或者是检讨目前的政策是否合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机会,但是目前需要时间来判断,短期内我认为风险资产可能会表现更好一点。但是目前过度单一的市场预期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记者:您之前说到如果经济增速到6.5%以下的话,也许会有政策上的调整。您在最后说您这边对中国经济年的增速预期是6.4%,这是否预期着您认为中国经济的政策拐点在年出现。如果出现,您觉得政策拐点最先出现和反映在哪个领域,是去杠杆还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调整?
周浩:这个问题很好,也是我个人也在问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到6.6%、6.7%的经济增速,对很多市场参与者并不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金融监管会进一步往前走,但对于长期的经济研究者也不是坏事,因为金融监管的确是需要进一步加强。
个人目前判断是,整个政策还是处于相对微妙的状况下,主要因为我们看到的经济增长可能是6.5%、6.4%,或者相对较高,但是过程中肯定会出现检讨,这个检讨是这样出现的:如果大家都认为经济这么好的话,那么PPI的上升会带来下游产品价格的上升,下游产品价格的上升会推高CPI。以前我们是PPI上,经济不好需求不旺盛,所以产品价格没有上来。如果PPI上升的状况下,下游的需求因为经济好转还是保持不错的话,那么CPI也会起来。CPI起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政策不能够放松只能收紧。加上去杠杆带来的货币政策的自然收紧,结果肯定是有一个经济部门承担高利率带来的代价,那么这是整个经济体还是部分经济部门,目前不好说。我只知道,当余额宝收益这么高,钱都放余额宝时,这会出现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悖论。
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投资现金是最准确的选择,我把钱放银行做理财是最正确的选择之一。但是,当所有人都把钱投资于现金,那这个经济的预期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好的话,就不会把钱放现金上。总有一点是错的。如果将这一逻辑梳理清楚,我们只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的确是把钱投资在现金上,这些人获得的现金相对比较高的收益,肯定是由另外一个部门承担的。这个部门要么是高杠杆的部门,要么是认为经济会好转的部门。经济会好转的部门带来的问题是CPI会起来,他愿意付更高的利率是因为可以得到更高的收益,CPI会起来,这会侵蚀他本身的收益。另外一个部门是它不断地付出更多的债务,这样的状况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政策的拐点肯定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出现,就是对经济的判断出现问题了。
因为这么多人投资现金,其实市场早就有经济不好的信号了。这种信号被更多人承认——可能一段时间后出现,现在暂时没有看到——出现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政策出现快速转向,就是认为高利率是不可持续的,高利率不可持续只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货币政策实际上在边际上出现放松,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如果货币政策出现一个明确的信号和转向的信号,可能意味着去杠杆的政策也会慢慢地降低力度。
财政政策上今年可能不会出现明显的加杠杆或加刺激的状况,这可能是历年来最少见的一次。过去很多年对经济的判断导致了财政政策相对刺激化。但是今年对经济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判断,可能导致财政政策在今年第一次真正显得中性。在这种状况下,也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向下的压力,只是短期内我们可能没有感受到而已。所以把这些放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我们目前认为经济会好转、杠杆会下来、去杠杆的经济政策会持续、导致利率会上升的这样一个判断肯定会有一点是无法支撑的。逻辑上肯定有一点是错的,要么是经济超预期,要么是利率超预期下降,这两点肯定会有一点发生变化。短期可能是经济超预期,但是中长期的话我认为是利率超预期下滑。
记者:第二个问题是您谈人民币在汇率上着力比较多,我想问中国央行今年是否会加息?
周浩: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市场可能会看到公开市场利率会有一定上调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加息几乎没有可能的。第一个是央行有意降低一年期存贷款利率的重要性。很多人说OMO就是更加市场化的操作,其实不是的,OMO是更加便利的操作,你今年上一个点、明年两个点,市场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加一次息加25个基点,央行可能会觉得对它来说承受的压力更大一点,但其实OMO是更加便利化的操作,同时它想调控的这人些,其实都看OMO,所以它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便利的操作方式。
另外一点我们真正要问自己的是,大多数人认为OMO今年会上调30、40个基点,现在2.7、2.8%的水平,可能会上升到3以上,这个合不合理?我个人认为不会到3%以上,弄不好最近的一次5个点的加息就是一个终点,这个不好说。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判断它是一个趋紧的过程,但是目前对于利率预期有过高的嫌疑,就像过去一段时间对利率预期有过低的嫌疑一样,目前国债利率达到过4%或者是4%以上,可能是相对过高的水平,不是可持续的状况,这是我的判断。
记者:最近我看了最新的数据,就是所谓的境外投资者连续9个月买中国的债创了新高,我仔细看了名单,其实里面35%是境内机构的境外分支,就是自己人。另外有20%是所谓的大中华区的,也就是港澳台。剩下的45%是相对比较纯的外资,但是也有新加坡华语区的。真正所谓大中华和港澳台占55%,超过一半。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纯西方的投资者对中国不够了解吗?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周浩:真正了解中国市场,愿意投资中国市场的,往往是在中国做过交易的债券交易员们,他们在海外做PM,他们的确也推动了这样一个资金的来源。另外一点本土偏好(HomeBias)是永远存在的,就是我永远投资于我熟悉的市场,亚洲的投资人愿意投资亚洲的债券市场,亚洲的投资人不愿意投资南美的债券市场,哪怕高收益也不愿投资,他们也用了一个理由说是持续不好,因为总要半夜起来做交易,其实是因为不了解。往往是南美的投资人最早抄到巴西市场的底,这是一个被动投资的过程。这是很自然的homebias的过程。很多人据此来分析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是不是真的国际化货币,或者人民币国际化是否走偏的问题,我觉得言过其实。欧元区也是一样的,买欧元区资产的最多也是欧元区以及欧元区相关的投资主体。哪怕欧元区利率再低他们也会投资自己相对熟悉的资产。
倒过来来说,目前除了是美元没有一个国际货币,只有美元是非常多元化的,美国可以将自己的债务转嫁给任何人,大家还想方设法地买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因为大家认可美国及美元资产的国际地位。所以除了美元资产以外,其他所有的资产都有本土偏好,不要说中国,买马来西亚资产的基本都是印度尼西亚或者东南亚的人。这是正常的过程,不必过度解读,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市场真实的、目前相对比较简单的交易结构。
记者:当年次贷危机以后,美国去杠杆比较剧烈。到年刚刚去完,也有很多银行破产。中国现在是慢慢去,还有一些配套的措施,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不知道这两种模式对比您认为有什么不一样。还有现在都在讨论银行要补充资本金,今年会不会更多的银行发债?
周浩:第二个问题是肯定的,因为很多银行资本金压力大。而资本金压力大主要来自于两个地方:一个是自己的资本金不够,最后怎么计算RWA(风险权重资产)的问题。因为中国很多金融机构风险权重资产的计算有很大的问题,他没有真实地告诉大家他有多少RWA。如果银监会让所有人都补充RWA的话,很多银行都会面临压力,补充资本金是必然趋势。如果股市好的话,这个趋势会更强烈一些,然后大家又说哪个银行发新股把股市打下来,其实银行不是的,也要看,如果你们价格好的话我也愿意多发一点。
这是一个文化性的问题,这就像欧洲的银行裁员节奏永远慢于美国的银行裁员一样的,美国的文化当中就认为要快,另外一些文化它就是认为要更缓慢一些,没有哪个比哪个好。最终结果要看经济到底有没有潜力,美国的经济只要有潜力无论怎样去杠杆最后都会爬起来。经济本身的基本面和本身的素质决定了经济的未来走势,短期的杠杆和政策只会影响到一些举措,而且每个经济体最后都会因为竞争力的强弱而实现自己的位置。我只知道美国快速去杠杆的模式不会被其他国家使用,这是美国企业文化决定的。就像其他公司的CEO永远挣不到美国公司CEO那么多钱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中国方面,我们只知道它会这样做下去,但是另外一点要提的是中国的杠杆率很难出现快速的下滑,中国的杠杆率很有可能出现的是相对平稳的态势,就像现在看到的债券市场的回购交易一样的。通过用时间和空间不断置换的过程来实现经济往前走或者经济实际的变化,根本上来说还要看中国经济有没有潜力。但是我还是认为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力大于很多经济体,这是我的看法。
(来源:财经网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处理)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ruseluosi.com/ljls/13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