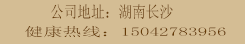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利息与价格 > 利息与价格内容 > 埃马纽埃尔bull加尼耶161
当前位置: 利息与价格 > 利息与价格内容 > 埃马纽埃尔bull加尼耶161

![]() 当前位置: 利息与价格 > 利息与价格内容 > 埃马纽埃尔bull加尼耶161
当前位置: 利息与价格 > 利息与价格内容 > 埃马纽埃尔bull加尼耶161
16-18世纪欧洲的社会与气候
埃马纽埃尔?加尼耶文周立红译
摘要:16-18世纪,面对洪水、干旱等气候灾害,欧洲社会认为是天上的神对有罪的生灵发泄愤怒,通常举行巡游,以表达对上帝的顺从。巡游在16世纪20年代增多,年逐渐减少,路易十四时期稍有回升,随后又渐趋消失。17世纪下半期起,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对应对气候灾害的举措产生怀疑,认为气候反常更多是自然原因造成,而不是出自上帝的审判。18世纪后期,法国王家医学协会建立,凭借信奉新希波克拉底主义的医生搭建了第一个国家层面的气候网络,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促成了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转向由理性和科学指引的世界。随着行政机器的增强,欧洲一些国家发展了有效的科学手段,逐渐承担起了应对气候危机的责任,也促成了危险意识的诞生。
关键词:气候;巡游;灾害;治理
基金项目:中山大学“年度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和中山大学青年教师重点培育项目“法国旧制度时期极端气候事件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8wkzd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埃马纽埃尔?加尼耶(EmmanuelGarnier),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贝桑松大学编年史-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简介:周立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鄱阳湖学刊》年04期。
气候及其带来的危险能成为研究对象吗?对法国历史学科来说,这是一个玄奥的问题。很早以前,法语世界的历史学家探讨复杂的生态系统时就掀起了这样一场经典的老辩论。自年勒华拉杜里出版皇皇巨著《公元一千年以来的气候史》以来,这个问题就周期性地搅动法国历史学界。事实上,许多法国历史学家总是在自问,从“总体”视野,即从气候、文化与社会视角研究气候是否恰当?如果气候史的文化维度可被容许,但若从科学史或观念史视角审视,其跨学科和系列史的特征又总是让他们中不少人困惑。其实,这些学者以不满的眼光看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认为这将使历史学家沦为气候学家或地球物理学家的替补队员。在年发表的探讨气候史的文章中,捷克历史学家布拉齐尔(RudolfBrazdil)毫不含糊地提醒学界注意,法国在开拓所谓的“欧洲历史气候学”中扮演的先锋角色。他一开始就强调,这门新的历史研究对象的奠基人勒华拉杜里的著作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方法论、解释以及对过去气候的历史重建方面。他是否还应该提醒学界注意这一点?勒华拉杜里年出版的《公元一千年以来的气候史》瞬间成为国外气候史研究的奠基石。相反,法国历史学界对该书的评价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勒华拉杜里:《公元一千年以来的气候史》五十多年过去了,气候在法国还是一个没有得到清晰识别的研究对象。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现代人对气候是否发生变化争论不休,气候史确实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视野反思乡村史或环境史。近二十来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气候史的“领洗池”虽说是在法国,这门研究却主要是在欧洲其他国家推陈出新。这里涉及法国的一个悖论。尽管法国历史学派的另一大师布罗代尔年以来就为气候史做了一些奠基工作,在他探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空间的博士论文里,他提出一个问题:“16世纪以来气候是否有变化?”凭借直觉,他推进了一个假设,即在阿尔卑斯山范围内,气候有过剧烈的波动。尽管他还没有承认,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整个地中海盆地。对气象造成的风险,气候学家用“极端”(extrême)形容,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势并不好。历史学家遭遇一种额外的障碍:社会学的遗产,尤其是贝克(UlrichBeck)的遗产对他们的反思施加了压力。在贝克年出版的奠基性著作里,他断言,灾害社会(sociétédescatastrophes)转变成了风险社会(sociétédurisque),他使传统的“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截然对立。在前现代社会,不存在风险,一种社会信念取而代之:各种各样的危险由完全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造成。贝克认为,工业社会与这种集体的宿命论不同。历史学家认为工业社会于19世纪50年代诞生,它根据支配(人)与被支配(自然)的关系,重新界定了它与自然环境的联系。工业化引发风险,但也凭着工具理性化和科学进步使贝克的界定和量化显得合理。社会学家认为,许多不专业的历史学家参与塑造了过去那个脆弱社会的神话,他们认为疾病、自然、政治、军事上的灾害统统是“神的愤怒”的暴力呈现。灾害社会VS气候风险社会?来自“神的愤怒”……16-18世纪,在“烈日炎炎’的夏季与西伯利亚冬季之间,洪水与瘟疫接连不断,人们很容易相信,天上的神对有罪的生灵发泄愤怒。人们把上帝发来的神迹看作懊悔的预兆。直到旧制度末期,宗教信仰仍然根深蒂固,尤其是在乡民们中间。民众的情感可由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解读,城乡社会的存续主要依赖乡村经济,而后者面对气候风险非常脆弱。惊慌失措的居民,遭遇不理解的、危及生存的灾害,只能用“万能的上帝”来解释。他们在狂风暴雨、蝗虫泛滥中,只听到愤怒的上帝发出的警告。他们把生活中的暴力看作上帝意志的展现。而唯一能缓解焦虑的,就是祈祷和弥撒,借此人们向上帝表达顺从。他们总是真诚地祈求上帝的帮助。如果心愿满足,则当祈祷有了效果。居民表达对上帝顺从的方式不一,祈祷最常见。祈祷或为求雨,或为止雨。人们祈祷冬天不要结冰,这对秋天播下的种子不利;人们祈祷春天不要阴凉潮湿,这会延缓种子发芽开花;人们祈祷夏天不要下雨,这会毁掉等待收货的农作物……18世纪40年代,贝桑松巴唐(Battant)街区的葡萄农反复请求神甫使用驱魔法驱散黄蜂!18世纪前三分之一个世纪夏天炎热,黄蜂迅速繁殖,危及葡萄采摘。实行驱魔法时,根本没有巫师出现。如果这些昆虫遭受这样一种惩罚,而不是“被开除教籍”,只是因为它们没有领受神恩,没有接受洗礼,就像那个时代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土耳其人、不信基督教者”……。除了这些小虫子,基督徒和他们的牧师还驱除暴风雨。年,布伊(Bouis)神甫在里昂出版《神甫的讲道台》,建议受到风神厄俄斯(Eole)威胁的教区居民由本地神甫实行驱魔法,驱散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仪式开始前,神甫由信徒抬到“地势高的地方,以便看清暴风雨起于哪个角落”。如果我们当代人把那些为了求雨或为了获得“宁静”而举行的祈祷,解读成泛灵论社会的神奇习俗,那是这么快就忘了天主教为求“上帝”的宽恕,举行而且总是举行一些许愿或赎罪仪式。可以说,为了应对气候灾害的巡游无处不在,调节着南欧信徒的宗教生活。历史学家掌握了一种材料,如果说是宗教性质的,倒不如说首先是行政性质的,其内容是对世俗生活的描述,借此可以重构巡游长时段的系列,并可研究它的变化。这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巡游不是出自教会的动议,而是市政机构的推动,这可由巴黎、图卢兹或巴塞罗那的市政决议证实。巴塞罗那的档案中保存的这类巡游可以后延到20世纪初!一旦政府部门做了决定,教会就在分包商或专家出身的税务区长官(élus)的请求下参与进来。请注意,游行是祈祷仪式,各个社会群体(宗教团体、法定团体、人民)鱼贯而行,背诵祈祷文,给上帝咏唱颂歌。他们想获得神恩,想风调雨顺,好“贮藏土地的果实”,这是那个时代的惯用语。中古以来,游行有助于让整个社会团体悉数参加,尽管游行仪式中还清晰地保留着某些社会不平等。放在历史背景下看,巡游是对气候危机的政治回应,不然,气候危机将转变成社会危机。传统上,市长受到“人民的声音的鼓动”,请求巴黎高等法院颁布法令,举行大巡游,以“平息上帝的怒火”。根据气候事件的严重程度和警察总监的态度,高等法院或颁布一则法令,查找圣人的遗骸盒,或者下达判决,让圣人即刻显灵。教区先举行五六次巡游,城市再举行大巡游。在巴黎,人们自13世纪以来,借助巴黎的保护人圣热娜维耶夫求助上帝保护。圣热娜维耶夫的遗骸盒遭受了种种磨难,年被存放到先贤祠,年被带到铸币厂熔化。至于遗骸盒里装的圣骨,没有能够抵御无套裤汉的圣像破坏运动,后者把它们扔到巴黎沙滩广场燃烧的一堆祭批和祝圣装饰里毁之一炬。使用计量方法分析巴黎的具体情况,有助于理解巡游的文化和社会进程。气候问题成为举行仪式的重要原因,40%以上的致敬圣热娜维耶夫的游行都是为了应对气候灾害,这个数据远远领先于捍卫王国、国王或宗教的巡游。如果我们对巴黎的宗教巡游按编年的顺序排列,这些宗教习俗的延续与断裂便可一目了然,也能展现对气候危机的宗教感知。近代,宗教巡游在16世纪20年代增多,年渐趋消失。之后,与摄政、三十年战争和投石党运动相连的政治动荡时期,虽然有接二连三的气候灾害,但巡游则没有经常举办。反之,路易十四亲政初年,巡游则稍有回升。从人力和财力支持来看,巡游不是在年而是在年5月达到高潮,那时正遭遇罕见的干旱。为了“贮藏土地的果实”,巡游组织起来,动员了巴黎大批民众和教士,税区长官(élus)确保任一等级都不缺席。个别情况下,国王和内廷也参与其中。巴黎市政档案和沙尔庞捷(Charpentier)神甫都记录下来这场巡游,这些史料也揭示出巡游在社会表征上的断裂。最初,巡游由民众倡议举行,乡下人和城里人到圣热娜维耶夫教堂汇合。后来,巴黎的市政官员(échevins)和司法官员(prév?t)想控制这种自发的巡游,便在举行仪式的第一时间下令打开主保圣人的遗骸盒,使巡游具有了政治意味。随后,市政、司法官员发现干旱持续久,民众的焦虑迟迟不能散去,便决定举行大巡游,组织形式与原来的仪式大有不同。路易十四时代过后,18世纪30年代起,巡游骤减,最后一次巡游在年举行。但这不应迷人耳目,实际上,它代表的不是古老宗教仪式的恢复,而是标志着它的彻底断绝。因为这一次,城市和当局把这种仪式忘得一干二净,只是大批乡民在神甫的指引下来到城里,倡议举办巡游活动,向圣人求雨。通常说,在宗教反应上,新教信仰对灾害的看法更具理性。确切的方法是考察新教对气候的解释是否具有特殊性。对所有信徒来说,不管他们的痛苦是否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灾害带来的,都会使其对上帝的信仰产生疑问。正如里斯本地震后,这种痛苦是否让人们质疑神圣的权力呢?这种神圣权力把自己定义为绝对权力。对加尔文而言,不能有任何怀疑,“人们习惯于把上帝对世界的治理称作天佑。”因此,加尔文全力反驳那些在16世纪为“上帝万能”观点辩论的人,这种观点认为上帝留给每个人自由意志,不直接干预他们的生活。于是,灾害就具有了现代含义,而不是上帝计划的标记。相反,日内瓦新教改革者捍卫的绝对权力(potestasabsoluta)不是“闲散”,而是时时刻刻体现在善恶之中。干旱、洪水,甚或饥荒,皆是神意展现。因而,人们认为加尔文教的信徒接受这些不幸是自然的灾祸,乃“有益的”恩赐,于是祈求上帝宽恕。然而,这并不禁止采取更世俗的(或者说更实用的)介入措施帮助灾民。日内瓦牧师会总是定期提醒“城市参事先生们”有责任推行基督教的赈济。-年遭遇严重气候危机,后者调控市场上小麦的价格。如果加尔文的日内瓦不举行巡游,人们则实行劝告或斋戒。年“悲苦之时”,牧师会号召信徒禁食,议会“先生们”予以肯定,让人礼拜天张贴这一劝勉词。此种方式随后得以推广,延续到18世纪末,总是得到市镇官员的“祝福”(bénédiction)。灾害具有教化功能,牧师借机重掌基督教社会。年地震后,牧师借助普遍恐慌,提醒信徒注意世界末日的信息,劝告人民视灾害的打击为上帝愤怒的警告。24年后,“天气紊乱”又启发牧师谴责信徒破坏了安息日的规定,礼拜天出城散步,更糟糕的是,频繁出入咖啡馆、酒馆,鲜少去教堂。牧师教导进入高潮后,就威胁说“上帝必施怒于人”。所幸,牧师认为,只要渎神的人“严格修正行为”,上帝就会被感化。不到一个世纪,已可发现加尔文主义对灾害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年4月,彗星划过天空,牧师弗卢努瓦(Flournoy)在日记里不再持有一种成见,即认为彗星的出现是上帝发出惩罚的信号,而是仅仅对这一现象做了描述性解释。如果我们知道,年6月,阿劳(Aarau)召开了一次新教会议,决定彗星出现时要进行忏悔,那么牧师弗卢努瓦的这种评论就属惊人之举了。当然,我们不能过于仓促地下结论,因为还有很多看法遵循的是加尔文宣扬的“绝对权力”的正统路线。17世纪80年代,学识渊博的斯蓬(JacobSpon)将那些因灾害而消亡的“繁荣之城”与日内瓦对立。斯蓬认为,日内瓦是加尔文主义的首都,多亏上帝“崇高的指引”,它才一直能免受灾害打击。更有甚者,哲学家伏尔泰和卢梭围绕“神意”(providence)展开激辩时,日内瓦人为了追念年的里斯本地震(瑞士年12月9日也发生了地震),决定在年2月19日禁食。年的里斯本地震
所谓现代社会?旧制度时期人们对气象现象的认知从传统到理性的断裂,发生在社会和思想领域,可以在档案文献里寻觅其踪。我们还需探讨观念转变的原因和过程,分析这样一种变化如何影响欧洲国家应对气候反常的政策。虽然没有充足的证据做统计,历史学家还是可以看出,17世纪下半期起,已经出现了对天主教和新教应对气候灾害举措的怀疑,如果不是谴责的话。那些独立思考的人(那个时代的神甫可能称这些人为异教徒)认为,气候反常更多是自然原因造成,而不是出自上帝的审判。一种新的世界观出现了,一种观念也在形成,即应该把上帝的意志与自然界的暴力区分开来。诺代(GabrielNaudé)年出版《政变论》,提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这位四分体(Tétrade)的创始人,“博学的不信教”(libertinageérudit)传统的始作俑者,指出“百姓愚昧,没有教养,各种欺诈学说来者不拒,即便有人提出对灾害的超自然解释,他们也会听进耳朵去的。”几乎在同一时代,南锡的某些资产者和贵族是那些呼唤圣西日斯贝(SaintSigisbert)求情的巡游的见证人,他们对这些活动的评论印证了这种观念的断裂。他们不只对这种信仰提出质疑,还谴责这些仪式为崇拜偶像,冒犯了心智开明之人。这种从神的单一原因解释气候灾害的信仰,是否在17世纪40年代走向衰落?这是肯定的。不过,这些边边角角的例子还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气象学世俗化的开端。17世纪上半期,某些心态发生了变化,但这只局限于小部分人,由于他们在社会上位居主导地位,所以有思想的自由。对于劳苦大众来说,祈祷、禁食、巡游仍照旧进行,他们还在相信,社会遭遇的不幸,出自上帝的惩罚。这些新型的思想趋向于接近“自然主义”,视自然及其要素为服从神意的工具。只从自然方面寻找解释,这种观念被接受的过程很慢。这一点可以这样解释:如果不幸不再是更高级的意志主宰,而是归于自然原因,那忏悔将没有用处,人将没有求助的对象。自然的观念要能进一步发展,就需要科学的气象学形成,并以保护型国家的出现作为必然结果。人们渐趋脱离造物主的支配,想法设法应付自然,并成为它的主人。这正是气候史的悖论,正如在兰斯隆重加冕的笃信王(SaMajestéTrèsChrétienne),成为欧洲的先锋。对气候的宗教解释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这也使历史学家发现,18世纪初起,日记或市镇决议中,几乎不再从上帝角度进行解释了。神甫的观念也发生了这种变化,看看教区记录簿上对暴风雨的记载,就能证实。伯尔尼的牧师号召他们的“羔羊”祈祷和忏悔,法兰西岛、香槟和阿尔萨斯神甫的钟楼没有躲过年1月的飓风,他们使用更理性的话语,详细地解释风力、方向及损害。难道我们还不能从中看出科学进步的结果吗?发现理性知识的普及形式吗?这种自然主宰的新理论要想得到肯定,就需要科学的支撑,因为它解释和衡量的内容不那么可怕,也不那么超自然。不过,旧制度最后一个世纪理性时代的降临加速了几个世纪以来的转向,即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转向由理性和科学指引的世界。当然,认为灾害出自上帝的愤怒,出自不能理解的命运,这种传统观念没有消失,仍旧在大众心中持续了很长时间。虽然心理学承认精英的观念真的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敢比较一下年弗吕蒂埃词典(DictionnairedeFuretière)和年特雷武词典(DictionnairedeTrévoux)对风的定义,就会相信心理学的结论。前一本词典仍旧提及“自然元素的主宰”,后一本则看到“空气从一个地方被推到另一个地方的多少有些暴力的运动”,区分了32种不同类型的风。此后,人们对规则而不是对神迹感兴趣。人们想测量这种恒量。达芬奇已经画出了风俗表和水位计。伽利略(-)的学生和门徒自16世纪末起,已经了解通过液体的膨胀测量温度的原理。“温度计”这个词年才出现,气压计(托利切利,帕斯卡)17世纪40年代出现。在法国,莫兰(LouisMorin)无疑是工具观测的先锋,他是巴黎的一个医生,-年间每天都进行气象记录。同一时期,雨量器和温度计接连在巴黎及其周围出现。不可怀疑,自17世纪70年代起,巴黎天文台和科学院对气象知识的传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早熟的个案证实,对大气气象的更清晰的思考不只是重农学派的特权,这可以否认福柯的说法,他认为“重商主义绝不会提出理性的诉求”。但的确,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世纪出现了不可逆的转向。以王家医学协会为模板,出现了很多科学协会。王家医学协会是由路易十六倡议,达济尔(Vicqd’Azyr)医生和科特神甫(PèreCotte)共同主持下创办的。欧洲其他国家也不例外,布雷斯劳(Breslau)医生卡诺尔德(JohanKanold)为中欧建立了一个网络,年朱林(JamesJurin)成为伦敦王家学院秘书。然而,在所有这些组织中,唯有年在莱茵的巴拉丁选帝侯创议下建立的巴拉丁气象协会可与法国的兄弟协会相抗衡,它们共同推动了欧洲气象知识的流转。这些协会主要由信奉新希波克拉底主义的医生组成,首要任务是揭示气候与健康的关系。它们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就像王家医学会年以来做的那样,搭建了第一个国家层面的气候网络。除了疾病分类学方面的报告,这些调查还收集了不计其数的表格,记录了温度、气压、水文方面的数据,还附有珍贵的对人和物的气象观察。科学的协同合作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提供给开明的公众,或者通过公开会议,或者作为巴黎科学院的研究报告(Mémoires),或者以气象学文章的形式定期出现在《巴黎日报》、《法国报纸》或德意志地区的《维也纳日报》。巴黎书商哈第从这些科学和传媒史料获取知识,他贪婪地阅读着王家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和《巴黎日报》上刊载的文章和气象表格。?图表1,摘自《巴黎日记》的气象表格,标明了(年1月1日)塞纳河河面的高度。实践:形态繁多的进程,走向“新的治理”国家发展了有效的科学手段,随着行政机器的增强,逐渐承担起了应对气候危机的责任。以前,人们若遭到极端气候事件的威胁,就向教会求助,这种态度受到世俗政权的鼓励,也加强了教会的传统救助使命。17世纪下半期,法国的情况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尤其是通过财政上的严加控制,君主制政府为对人口的持久的行政管理奠定了基础。即便君主制政府能支撑起那时的军事需要,财政政策还是使王国侵入原本属于神职人员的领域,也在某些程度上侵入市政掌管的领域。很长时间以来,教士或市镇机构采取特别捐款(donsexceptionnels)、宗教游行和财政手段应对自然灾害。那些地方主义盛行的省,诸如法国的布列塔尼,西班牙的加泰罗纳,不间断地以习惯为名,暗中角力,对抗国王的补偿政策。因此,衡量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理解促成福利国家(étatProvidence)在19世纪诞生的动力和过程,构成了一个学术挑战,也催生了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除了要对气候的内容进行探讨外,还需要研究对立力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它们之间的对抗和妥协。因此,如果我们采用整体视角,就不能不参照欧洲大陆的情况。管理气候危机及其社会后果(粮缺、骚动),依赖于一套针对领土保护和发展的更广泛的话语。为什么不看看米切尔?德尔(MitchellDean)指出的“人与物关系”变化的萌芽呢?德尔认为,国家的治理依靠更直接的介入,以改善人口的环境境遇。这样的学说必然通过政府机构在中央权力与国民之间关系的“超越性”来论证,依据的是福柯定义的“规训”(discipline)原则。这种超越性产生了一种向心的动力,“隔离出一个空间”(例如法兰西王国)。然而,如果“隔离出一个空间”,为的是施加国家权力,那也相应推行了专业政策。在气候方面,进行了统计或科学的研究,巴黎天文台、王家科学院或王家医学院这些机构是这种政策的明证。米歇尔·福柯圣热纳维耶夫,重农学派与饥荒阴谋对于公共权力来说,首先,为了供给市场,各地总督自18世纪40年代以来,对收成状况开展了大规模的系统调查。每年,总督助理撰写收成状况报告,预测是否会出现谷物短缺,以平息社会冲突。短缺首先对当局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它往往因下雨或干旱这样的气候灾害而造成。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短缺还意味着君主及其臣民的不幸。小麦短缺能煽动起各种类型的骚乱,自近代以来动员起自城镇到中央的权力机构。不过,行政和社区在“预防-警戒-救援”三部曲的范围内进行动员的形式值得持久的转载请注明:http://www.ruseluosi.com/ljnr/10165.html